诫兄子严敦书
援兄子严、敦,并喜讥议,而通轻侠客。援前在交趾,还书诫之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恶之甚矣,所以复言者,施衿结缡,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
“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讫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我的兄长的儿子马严和马敦,都喜欢讥讽议论别人的事,而且爱与侠士结交。我在前往交趾的途中,写信告诫他们:“我希望你们听说了别人的过失,像听见了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听见,但嘴中不可以议论。喜欢议论别人的长处和短处,胡乱评论朝廷的法度,这些都是我深恶痛绝的。我宁可死,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孙有这种行为。你们知道我非常厌恶这种行径,这是我一再强调的原因。就像女儿在出嫁前,父母一再告诫的一样,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啊。”
“龙伯高这个人敦厚诚实,说的话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指责的。谦约节俭,又不失威严。我爱护他,敬重他,希望你们向他学习。杜季良这个人是个豪侠,很有正义感,把别人的忧愁作为自己的忧愁,把别人的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无论好的人坏的人都结交。他的父亲去世时,来了很多人。我爱护他,敬重他,但不希望你们向他学习。(因为)学习龙伯高不成功,还可以成为谨慎谦虚的人。正所谓雕刻鸿鹄不成可以像一只鹜鸭。一旦你们学习杜季良不成功,那就成了纨绔子弟。正所谓“画虎不像反像狗了”。到现今杜季良还不知晓,郡里的将领们到任就咬牙切齿地恨他,州郡内的百姓对他的意见很大。我时常替他寒心,这就是我不希望子孙向他学习的原因。”
注释
讥议:讥讽,谈论。
通轻侠客:通,交往;轻,轻佻;与侠士轻佻之人交好。
交趾:汉郡,在今越南北部。
汝曹:你等,尔辈。
是非:评论、褒贬。
正法:正当的法制。
大恶:深恶痛绝。
施衿结缡,申父母之戒:衿:佩带。缡:佩巾。古时礼俗,女子出嫁,母亲把佩巾、带子结在女儿身上,为其整衣。父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无违命。”母戒女曰:“戒之敬之,夙夜无违宫事。”
龙伯高敦厚周慎:龙伯高这个人敦厚诚实;龙伯高:东汉名士,史书上记载其““在郡四年,甚有治效”,“孝悌于家,忠贞于国,公明莅临,威廉赫赫”。周慎:周密,谨慎。
口无择言:说出来的话没有败坏的,意为所言皆善。 择:通“殬(dù)”,败坏。
杜季良:杜季良,东汉时期人,官至越骑司马。
清浊无所失:意为诸事处置得宜。
数郡毕至:很多郡的客人全都赶来了。
谨敕:谨敕:谨慎。
鹄:天鹅。鹜:野鸭子。此句比喻虽仿效不及,尚不失其大概。
画虎不成反类狗:比喻弄巧成拙。
下车:指官员初到任。切齿:表示痛恨。
以为言:把这作为话柄。
参考资料:
创作背景
汉代士人生存环境的险恶与变幻莫测使人时刻保持戒惧状态,谦虚、谨慎以求保全自我, 从而保证家族的延续和发展。因此,汉代士人们把这种戒惧意识在诫文中转化为对修身养德的强调。此封家书就是经典事例。更可贵的是,马援写这封家书给严敦二侄时,正是他率军远征交趾的时候。
参考资料:
鉴赏
马援的侄子马严、马敦平时喜讥评时政、结交侠客,很令他担忧,虽远在交趾军中,还是写了这封情真意切的信。文章出语恳切,言词之中饱含长辈对晚辈的深情关怀和殷殷期待,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原因有三。
其一、以“汝曹”称子侄,在文中反复出现,使子侄们在阅读时倍感亲切。不远千里致书教谕,也能收到耳提面命的效果。同一称谓反复出现,固然可使被称者自感受到重视,而更重要的是,作者选用的这一称谓也传达出丰富的信息。古人名、字并行,各有其用。一般长辈称晚辈用名,同辈相称则用字,如果“尔”“汝”相称,往往是不礼貌的,但在特定场合下却又能用以表示亲近,如韩愈《听颖师弹琴》“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句。作者在信中不依常规称呼子侄,却以“汝曹”相称,这就显得随和、亲切,拉近了长辈和晚辈之间的距离。被称的晚辈则可以从中体会到长辈的真情关怀。
其二、苦口婆心,现身说法,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晚辈沟通,而不是空讲大道理。如首段说“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只说自己如何,但是态度明确,感情浓烈,自然可以感染晚辈,又何必命令式地不许这不许那呢?至于“施衿结缡”句,更是反复叮咛,语重心长,使人感动不已。次段对当世贤良的作为得失加以对比评析,都是自己观察社会人生得来的经验之谈。其“刻鹄不成尚类鹜”、“画虎不成反类狗”的比喻,警拔有力,发人深省,是传之千古的警句。而诸如“愿汝曹效之”、“不愿汝曹效也”的话,虽然只是表示希望,但是字里行间满盈着真挚的关爱,比之“汝曹当效之”、“汝曹勿效也”这样板着面孔的口吻真不知要强过多少倍了!
其三、文中大量而恰当地使用句末语气词,起到了表达意义以简驭繁,只着一字而含义丰富;表达感情以无胜有,不着情语而情尤真、意尤切的突出效果。文中用“也”表达自己的肯定和期望,态度坚绝;用“矣”、“耳”表达自己的爱憎倾向,情深意长;用“者也”,则表达出对评说对象有所保留或不以为然。这些合在一起,不仅读来语气抑扬,更能使人由此领会充盈在文字背后的教诲、期望、关怀和爱护。
参考资料:
马援(前14年-49年),字文渊,扶风郡茂陵县。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著名军事家,东汉开国功臣之一。新朝末年,马援投靠陇右军阀隗嚣麾下,甚得其器重。后归顺光武帝刘秀,为刘秀统一天下立下了赫赫战功。统一之后,马援虽已年迈,但仍请缨东征西讨,西破陇羌,南征交趾,北击乌桓,官至伏波将军,封新息侯,世称“马伏波”。建武二十五年(49年),马援在讨伐五溪蛮时身染重病,不幸逝世。死后遭人构陷,被刘秀收回新息侯印绶,直到汉章帝时才获得平反,追谥“忠成”。唐德宗时,成为武成王庙六十四将之一。宋徽宗时被加封为忠显佑顺王,位列武庙七十二将。清圣祖时从祀历代帝王庙。
值暮景烟花领袖,点秋霜风月班头,少年狂翻作老来羞。有人处把些礼数,无人处结遍绸缪,任谁问休道咱共你有。假认义做哥哥般亲厚,行人情似妹妹般追逐,着小局断儿包藏着鬼胡由。明讲着昆仲礼,暗结了燕莺俦,似恁般谁猜疑我共你有。袄庙火既烧着皮肉,蓝桥水已淹过咽喉,紧按捺风声满南州。便毕罢了终是点污,若成合了到敢风流,不恁么呵也道是有。会云雨风也教休透,闲是非屁也似休偢,去那无缝锁上十字儿纽一个封头。由那快抡锹的闪着手腕,散楚的叫破咽喉,俺两个痛关心的情越有。期白昼家前院后,约黄昏雨歇云收,知他是你卖风他负德我胡搊。由你义秧儿栽个强证,草本儿指个牵头,见如今他共我有。题桥志文章锦绣,驾车心体态温柔,女貌郎才忒风流。语言间情暗许,眼色内意相投,两个委实无人道做有。口儿块特婪侃嗽,脚儿勤推恋俳优,每日家弄子里茶坊中紧相逐,为俺待的厚,也惼气快要的恶也忒情熟,因此上外人观恰便似有。闲谈笑踏科儿寻斗,但离别觅缝儿承头,好一会弱一会厮奚酬。着厮拾啜为了题目,闲打骂做了开头,两个虎难当又真个有。乔断案村俫杂嗽,望梅花子弟单兜,侧脚里姨夫做了冤仇。苏小小弃了舞榭,许盼盼闭上歌楼,似恁么难厮着怎做得有。实镘的剐皮割肉,虚恩情撇闪提鼻勾,乾遇讪乔敷演几时休。妆砌末招人谤,哮孛郎儿人羞,强折证刚道他有。
折垂杨都是残枝,诗满银笺,酒劝金卮。自在庐山,君游鄂渚,两地相思。白鹿洞谁谈旧史?黄鹤楼又有新诗。拈断吟髭,笑把霜毫,满写乌丝。
别友
唾珠玑点破湖光,千变云霞,一字文章。吴楚东南,江山雄壮,诗酒疏狂。正鸡黍樽前月朗,又鲈莼江上风凉!记取他乡,落日观山,夜雨连床。宰金头黑脚天鹅,客有钟期,座有韩娥。吟既能吟,听还能听,歌也能歌。和《白雪》新来较可,放行云飞去如何?醉睹银河,灿灿蟾孤,点点星多。倚蓬窗无语嗟呀,七件儿全无,做甚么人家?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酱瓮儿恰才梦撒,盐瓶儿又告消乏。茶也无多,醋也无多。七件事尚且艰难,怎生教我折柳攀花?
客窗清明
风风雨雨梨花,窄索帘栊,巧小窗纱。甚情绪灯前,客怀枕畔,心事天涯。三千丈清愁鬓发,五十年春梦繁华。蓦见人家,杨柳分烟,扶上檐牙。
雨窗寄刘梦鸾赴宴以侑樽云
妒韶华风雨潇潇,管月犯南箕,水漏天瓢。湿金缕莺裳,红膏燕嘴,黄粉蜂腰。梨花梦龙绡泪今春瘦了,海棠魂羯鼓声昨夜惊者。极目江皋,锦涩行云,香暗归潮。
赠张氏天香善填曲时在阳羡莫侯席上
月明一片缃云,揉做清芬,吹下昆仑。胜浅浅兰烟、靠靠花雾、淡淡梅魂。这气昧温柔可人,那风流旖旎生春。声迹相闻,多少余芳,散在乾坤。
自述
华阳巾鹤氅蹁跹,铁笛吹云,竹杖撑天。伴柳怪花妖、鳞祥凤瑞、酒圣诗禅。不应举江湖状元,不思凡风月神仙。断简残编,翰墨云烟,香满山川。
张谦斋左辖席上索赋
卷鲸川吸尽春云,曲妙重歌,酒冷还温。裁甚乌纱,尽他白发,醉个红裙。想献玉遭刑费本,算挥金买笑何村,俯仰乾坤,多少英雄,不到麒麟。
寄远
怎生来宽掩了裙儿,为玉削肌肤,香褪腰肢。饭不沾匙,睡如翻饼,气若游丝。得受用遮莫害死,果实诚有甚推辞?乾闹了若干时。草本儿欢娱,书彻货儿相思。
云雨期一枕南柯,破镜分钗,对酒当歌。想驿路风烟、马头星月,雁底关河。往日个殷勤访我,近新来憔悴因他.淡却双蛾,哭损秋波,台候如何?忘了人呵。
越楼见姬梳洗已倚立娇困若不胜情因记隔朱楼杨柳青青,烟锁窗纱,风动帘旌。爱镜睹婵娟、粉吹旖旎、玉立娉婷。翘凤头金钗整整,朵松花云髻亭亭。个样心情,困托香腮,斜倚云屏。登澄江君山有平原君墓并手植桧至绝顶甚壮人气宇芙蓉城古意山川,葬玉当时,植桧何年?江树阴阴,江帆隐隐,江草芊芊。蘸海渎东南半天,望金焦西北双拳。巾袂蹁跹,不索浮莲,挟取飞仙。
红梅徐德可索赋类卷
从来不假铅华,试耍学宫妆,醉笑吴娃。返老还童,脱胎换骨,饱养烟霞。罗浮梦休猜做杏花,萼绿仙曾服甚丹砂?春在天涯,紫蜡封香,寄与谁家。
帘内佳人瞿子成索赋
鲛绡不卷闲情,翠织玲珑,玉立聘婷。倚动银钩,耍吹罗带,笔振金铃。迷楚云花昏柳瞑,隔湘烟水秀山明。楼外人行,休放春愁,难掩风声。
西湖忆黄氏所居
多时不到儿家,想绳挂秋千、弦断琵琶、眉淡兰烟、钗横梭玉、粉褪铅华。软龙绡尘蒙宝鸭,烂胭脂雨过金沙。隔个窗纱,梦断东风,门外啼鸦。
贾侯席上赠李楚仪
洗妆明雪色芙蓉,默默情怀,楚楚仪容。甚烟雨江头,移根何在,桃李场中。尽劣燕娇莺冗冗,笑落花飞絮濛濛。湘水西东,怅望蹇衣,玉立秋风。
登姑苏台
百花洲上新台,帘吻云平,图画天开。鹏俯沧溟,蜃横城市,鳌驾蓬莱。学捧心山颦翠色,怅悬头土湿腥苔。悼古兴怀,休近阑干,万丈尘埃。
会州判文从周自维扬来道楚仪李氏意
文章杜牧风流,照夜花灯,载月兰舟。老我江湖,少年谈笑,薄幸名留。赠杨柳人初病酒,采芙蓉客已惊秋。醉梦悠悠,雁到南楼,寄点新愁。
赠罗真真
罗浮梦里真仙,双锁螺鬟,九晕珠钿。晴柳纤柔,春葱细腻,秋藕匀圆。酒盏儿里殃及出些腼腆,画巾争儿上换下来的婵娟。试问尊前,月落参横,今夕何年?
富子明寿
梨花院羯鼓挝晴,恰暮雨黄昏、新火清明。歌倚缑笙,香温汉鼎,酒暖吴橙。贺绿鬓朱颜寿星,是轻衫矮帽书生。趁取鹏程,快意风云,唾手功名。
丙子游越怀古
蓬莱老树苍云,不黍高低,狐兔纷坛。半折残碑,空余故址,总是黄尘。东晋亡也再难寻个右军,西施去也绝不见甚佳人。海气长昏,啼鴂声乾,天地无春。隔楼所见对望终日其媪若厌者遂下帘以蔽之织湘江一片波纹,窣下闲愁,隔断诗魂。非雾非烟,影娥池上,香梦无痕。拍画阑纤舒玉笋,启纱窗推晒罗裙。饱看娇春,倩得南薰,卷起梨云。
七夕赠歌者
崔徽休写丹青,雨弱云娇,水秀山明。箸点歌唇,葱枝纤手,好个卿卿。水洒不著春妆整整,风吹的倒玉立亭亭。浅醉微醒,谁伴云屏?今夜新凉。卧看双星。
黄四娘沽酒当垆,一片青旗,一曲骊珠。滴露和云,添花补柳,梳洗工夫。无半点闲愁去处,问三生醉梦何如。笑倩谁扶?又被春纤,搅住吟须。秋日湖山偕白子瑞辈燕集赋以俾歌者赴拍侑樽秋声一片芦花,正落日山川,过雨人家。羡歌舞风流、太平时世、诗酒生涯。待杨柳晴春风跃马,且桂华凉夜月乘槎。一曲吴娃,笑煞江州泪满琵琶。
感兴
谢安江左优游,梦觉东山,声动南州。覆雨翻云,怜花宠柳,未肯回头。成时节衣冠冕旒,败时节笞杖徒流,问甚么恩仇。山塌虚名,海阔春愁。
秋思
红梨叶染胭脂,吹起霞绡,绊住霜枝。正万里西风,一天暮雨,两地相思。恨薄命佳人在此,问雕鞍游子何之。雁未来时,流水无情,莫写新诗。
秋日与高敬臣胡善甫辈饮湖楼即事
疏帘外暮雨西山,唤起诗仙,共倚阑干。杯影涵秋,歌声送晚,鬓脚生寒。添风韵春纤象板,减恩情罗扇龙檀。红藕花残,茉莉双鬟,油壁吹香,催上归鞍。
劝求妓者
溺盆儿刷煞终臊,待立草为标,现世生苗。时下收心,眼前改志,怎换皮毛?厌禳死花枝般老小。踢腾尽铜斗般窠巢。日夜煎熬,要撅断琴弦,别觅鸾胶。
问春
东君去也如何?风皱纤鳞,烟抹羞蛾。恨白眼相看,青春不管,黑发无多。香絮引鱼吞绿波,落花惊蝶梦南柯。随处行窝,载酒吴船,击筑秦歌。
毗陵张师明席上赠歌妓周氏宜者
宜歌宜舞宜妆,道是风流,果不寻常。粉靥堆春,金盘捧露,翠袖笼香。此际相逢蕊娘,个中谁是周郎?愁近清觞,泥醉归来,灯影昏黄。
咏红蕉
红蕉分钟天涯,换叶移根,灌水壅沙。娇耐秋风,清宜夜雨,艳若春华。翠袖捧银台绛蜡,绿云封玉灶丹霞。富贵人家,妆点湖山,吃喜窗纱。仲明同知坦然斋集苏老琵琶吴国良箫歌者王玉莲坦然对客高轩,烂醉梅边,占得春先。箫阮鸾声,琵琶凤尾,宝鼎龙涎。金错落三分酒浅,玉玲珑一串珠圆,谁似尊前,谈笑风流,富贵神仙。
荆溪即事
问荆溪溪上人家,为甚人家,不种梅花。老树支门,荒蒲绕岸,苦竹圈笆。寺无僧狐狸样瓦,官无事鸟鼠当衙。白水黄沙,倚遍阑干,数尽啼鸦。
高敬臣病
赋高唐何事悲秋?山在书屏,云在帘钩。尽汗漫羁情,炎凉世态,万象蜉蝣。杨柳阴吴船载酒,藕花凉楚客登楼。宾主相留,且对清江,抖擞诗愁。
晋云山中奇遇
赚刘郎不是桃花,偶宿山溪,误到仙家。腻雪香肌,碧螺高髻,绿晕宫鸦。掬秋水珠弹玉甲,笑春风云衬铅华。酒醒流霞。饭饱胡麻,人上篮舆,梦隔天涯。爱秋娘弄月无痕,冰雪凝妆,风露为魂。歌颤鸾钗,尘随鸳袜,酒污猩裙。巧画柳双眉浅颦,笑生花满眼娇春。好客东君,特与新诗,留取香云。
西岩所见
西岩楼外东风,曲曲阑干,小小帘栊。甚午困懵腾,髻鬟髟妥鬌,星眼朦胧。正落絮飞花冗冗,又夕阳流水溶溶。金缕香绒,倦绣屏床,误却春工。
登毗陵永庆阁所见
忽飞来南浦娇云,背影藏羞,忍笑含颦。绕鬓兰烟,沾衣花气,恼梦梅魂。似湘水行春洛神,遇天台采药刘晨。愁缕成痕,一枕余香,半醉黄昏。
宴支园桂轩
碧云窗户推开,便敲竹催茶,扫叶供柴。如此风流,许多标致,无点尘埃。堆金粟西方世界,散天香夜月亭台。酒令诗牌,烂醉高秋,宋玉多才。
风雨登虎丘
半天风雨如秋,怪石於菟,老树钩娄。苔绣禅阶,尘粘诗壁,云湿经楼。琴调冷声闲虎丘,剑光寒影动龙湫。醉眼悠悠,千古恩仇。浪卷胥魂,山锁吴愁。
游琴川
海虞雄踞山州,水濑丝桐,路列文楸。铺翠峰峦,染云林障,推月潮沟。有第四科贤哲子游,是几百年忠孝何侯。舞榭歌楼,酒令诗筹,官府公勤,人物风流。
重九后一日游蓬莱山
重阳雨冷风清,阻却王宏,淡了渊明。昨日寒英,今朝香味,未必多争。蜂与蝶从他世情,酒和花快我平生。纵步蓬瀛,会此同盟,醉眼青青。
拜和靖祠双声叠韵
至当时外士山祠,渐次南枝,春事些儿。枫渍殷脂,蕉撕故纸,柳死荒丝。目寒涩雄雌鹭鸶,翅参差母子鸬鹚。再四嗟咨,捻此吟髭,弹指歌诗。
安溪半江亭陪雅斋元帅饮
半江亭上凭阑,挝鼓楼船,弭节江湾。金虎悬符,玉龙立槊,竹树生寒。绿波转秋回俊眼,翠云堆晚列歌鬟。樽酒开颜,如此江山,人在蓬壶,图画中间。
泊青田县
白鹤飞下青田,叹物换星移,谷变陵迁。山瘦披云,溪虚流月,今夕何年?梦已到石门洞天,眼休惊辽海人烟。谁与周旋?虎节元臣,乌帽诗仙。
自叙
斗牛边缆住仙槎,酒瓮诗瓢,小隐烟霞。厌行李程途,虚花世态,潦草生涯。酒肠渴柳阴中拣云头剖瓜,诗句香梅梢上扫雪片烹茶。万事从他,虽是无田,胜似无家。
毗陵晚眺
江南倦客登临,多少豪雄,几许消沉。今日何堪,买田阳羡,挂剑长林。霞缕烂谁家昼锦,月钩横故国丹心。窗影灯深,磷火青青,山鬼喑喑。
别有凌空一叶,泛清寒、素波千里。珠房泪湿,明珰恨远,旧游梦里。羽扇生秋,琼楼不夜,尚遗仙意。奈香云易散,绡衣半脱,露凉如水。
陈浩然招游观音山,宴张氏楼。徐姬楚兰佐酒,以琵琶度曲。郯云台为之心醉。口占戏之。
春江暖涨桃花水。画舫珠帘,载酒东风里。四面青山青似洗,白云不断山中起。
过眼韶华浑有几。玉手佳人,笑把琶琶理。枉杀云台标内史,断肠只合江州死。
 马援
马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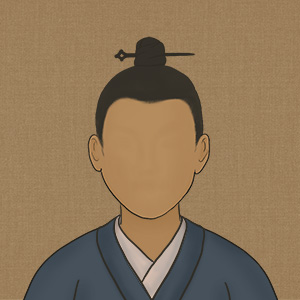 曾瑞
曾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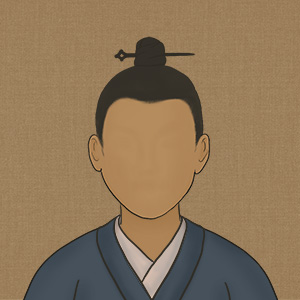 周德清
周德清 乔吉
乔吉 马致远
马致远 杜安世
杜安世 杨基
杨基 唐玨
唐玨 顾德辉
顾德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