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蕙兰花散花出阵阵幽香,雪后的晴空,辉映着池沼馆阁犹如画景风光。春风吹到精美的歌楼舞榭,到处是笙箫管乐齐鸣。琉璃灯彩光四射,满城都是笑语欢声。而今随随便便挂上几盏小灯,再不如昔日士女杂沓,彩灯映红了尘埃迷天漫地,车水马龙,万众欢腾。何况近年来我已心灰意冷,再也没有心思去寻欢逛灯。
江城冷落人声寂静,听鼓点知道才到初更,却已是如此的冷清。请问谁能向天公,再度讨回以前的繁荣升平?我剔除红烛的残烬,只能在梦境中隐隐约约重见往年的情景。人来人往,车声隆隆,手持罗帕的美女如云。我正想用吴地的银粉纸,闲记故国元夕的风景,以便他日吊凭。我笑叹那邻家梳着黑发的姑娘,凭倚窗栏还在唱着“夕阳西下”!
注释
女冠子: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唐词内容多咏女道士。今存词中,小令始于温庭筠,双调四十一字,上阕平仄韵换协,下阕平韵。长调始于柳永,双调一百十一字,仄韵。
蕙:香草名。
雪晴:雪止天晴。
池馆:池苑馆舍。
宝钗楼:唐宋时咸阳酒楼名。此处泛指精美的楼阁。
笙箫:笙和箫。泛指管乐器。
琉璃:指灯。宋时元宵节极繁华,有五色琉璃灯,大者直径三四尺。
暗尘明月:指元宵节灯光暗淡。
元夜:元宵。
蛾儿:闹蛾儿,用彩纸剪成的饰物。
初更:旧时每夜分为五个更次。晚七时至九时为“初更”。
灺(xiè):没点完的蜡烛;也泛指灯烛。
钿车:用金宝嵌饰的车子。
罗帕:丝织方巾。旧时女子既作随身用品,又作佩带饰物。
吴笺:吴地所产之笺纸。常借指书信。
银粉砑(yà):碾压上银粉的纸。
参考资料:
赏析
元宵佳节是历代词人经常吟咏的话题。不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在所有的节日中,以元宵最为热闹,也以元宵最为人所重。而在国破家亡之时,这个节日又最容易引起人们对往昔繁盛的追忆,最易牵动人们的故国之思。
全词起笔“蕙花香也。雪睛池馆如画”,即沉入了对过去元夕的美好回忆:兰蕙花香,雪霁天晴,亭台楼阁之中池波荡漾,街市楼馆林立,宛若画图,尽是一派迷人景象。极度地渲染了元宵节日氛围。“春风飞到,宝钗楼上,一片笙箫,琉璃光射。”春风和煦,酒旗飘拂,笙箫齐奏,仙乐风飘。据载,宫中曾做五丈多高的琉璃灯,又地方进贡之灯“或以五色琉璃而成”。那令人陶醉的音乐,那壮观的灯市,使词人忆起如昨天一般。
“而今灯漫挂。不是暗尘明月,那时元夜。”“而今”二字是过渡,上写昔日情景,下写当日元夕景况。“灯漫挂”,指草草地挂着几盏灯,与“琉璃光射”形成鲜明的对照。“不是暗尘明月,那时元夜。”既写此夕的萧索,又带出昔日的繁华。“暗尘明月”用唐苏味道《上元》“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诗意。以上是从节日活动方面作今昔对比。“况年来、心懒意怯,羞与蛾儿争耍。”今昔不同心情的对比。蛾儿,即闹蛾儿,用纸剪成的玩具。写当日的元宵已令人兴味索然,心境之灰懒,更怕出去观灯了。这种暗淡的心情是近些年来才有的,是处境使然。
下阕“江城人悄初更打”,从灯市时间的短促写今宵的冷落,并点明词人度元宵所在地——江城。下面数句直至词末,一连用了“问”、“但”、“待把”、“笑”等几个领字,一气直下,写出了自己内心的悲恨酸楚。“问繁华谁解,再向天公借”,用倒装句法,提出有谁能再向天公借来繁华呢?“剔残红灺。但梦里隐隐,钿车罗帕。”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词人剔除烛台上烧残的灰烬入睡了。梦中那辚辚滚动的钿车、佩戴香罗手帕的如云士女,隐隐出现。
“吴笺银粉砑。待把旧家风景,写成闲话。”以最精美的吴地的银粉纸,把“旧家风景”写成文字,以寄托自己的拳拳故国之思。银粉砑,碾压上银粉的纸。旧家风景,借指宋朝盛事。听到邻家的少女还在倚窗唱着南宋的元夕词。现在居然有人能唱这首词,而这歌词描绘的繁华景象和“琉璃光射”、“暗尘明月”正相一致。心之所触,心头不禁为之一动,略微感到一丝欣慰,故而以一“笑”字领起。但这“笑”中实在含有无限酸楚。,因为“繁华”毕竟是一去不返了。
这首词风格较为自然,词意始终在流动中,无一凝滞。但是在顿挫中显流动,于追琢中出自然。对过去元夕的铺叙作者不惜篇幅,不惜浓墨重彩,或直接描绘,或间接叙写,或通过梦境加以再现,着力处皆词人所钟之情。
参考资料:
创作背景
参考资料:
蒋捷(约1245~1305后),字胜欲,号竹山,南宋词人, 宋末元初阳羡(今江苏宜兴)人。先世为宜兴大族,南宋咸淳十年(1274)进士。南宋覆灭,深怀亡国之痛,隐居不仕,人称“竹山先生”、“樱桃进士”,其气节为时人所重。长于词,与周密、王沂孙、张炎并称“宋末四大家”。其词多抒发故国之思、山河之恸 、风格多样,而以悲凉清俊、萧寥疏爽为主。尤以造语奇巧之作,在宋季词坛上独标一格,有《竹山词》1卷,收入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彊村丛书》本,又《竹山词》2卷,收入涉园景宋元明词续刊本。
霍光,字子孟,票骑将军去病弟也。父中孺,河东平阳人也,以县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侍者卫少儿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毕归家,娶妇生光,因绝不相闻。久之,少儿女弟子夫得幸于武帝,立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贵幸。既壮大,乃自知父为霍中孺,未及求问,会为票骑将军击匈奴,道出河东,河东太守郊迎,负弩矢先驱至平阳传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趋入拜谒,将军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为大人遗体也。”中孺扶服叩头,曰:“老臣得托命将军,此天力也。”去病大为中孺买田宅奴婢而去。还,复过焉,乃将光西至长安,时年十余岁,任光为郎,稍迁诸曹侍中。去病死后,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 征和二年,卫太子为江充所败,而燕王旦、广陵王胥皆多过失。是时上年老,宠姬钩弋赵倢伃有男,上心欲以为嗣,命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枭尊号,是为孝昭皇帝。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遗诏封光为博陆侯。
光为人沉静详审,长才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须髯。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初辅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闻其风采。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众庶莫不多光。
光与左将军桀结婚相亲,光长女为桀子安妻,有女年与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盖主内安女后宫为倢伃,数月立为皇后。父安为票骑将军,封桑乐侯。光时休沐出,桀辄入代光决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长公主。公主内行不修,近幸河间丁外人。桀、安欲为外人求封,幸依国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许。又为外人求光禄大夫,欲令得召见,又不许。长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数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惭。自先帝时,桀已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并为将军,有椒房中宫之重,皇后亲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顾专制朝事,由是与光争权。
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怀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盐铁,为国兴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于是盖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与燕王旦通谋,诈令人为燕王上书,言光出都肄羽林,道上称跸,太官先置;又引苏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而大将军长史敞亡功为搜粟都尉;又擅调益莫府校尉;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臣旦愿归符玺,入宿卫,察奸臣变。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从中下其事,桑弘羊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书奏,帝不肯下。
明旦,光闻之,止画室中不入。上问:“大将军安在?”左将军桀对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诏召大将军。光入,免冠军顿首谢,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将军之广明,都郎属耳。调校尉以来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将军为非,不须校尉。”是时帝年十四,尚书左右皆惊,而上书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惧,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听。
后桀党与有谮光者,上辄怒曰:“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复言,乃谋令长公主置酒请光,伏兵格杀之,因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事发觉,光尽诛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盖主皆自杀。光威震海内。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独有广陵王胥在,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言合光意。光以其书视丞相敞等,擢郎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诏,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
贺者,武帝孙,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乱。光忧懑,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给事中,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鄂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离席按剑,曰:“先帝属将军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如令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
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承明殿,诏诸禁门毋内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还,乘辇欲归温室,中黄门宦者各持门扇,王入,门闭,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为?”大将军跪曰:“有皇太后诏,毋内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惊人如是!”光使尽驱出昌邑群臣,置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安世将羽林骑收缚二百余人,皆送廷尉诏狱。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谨宿卫,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负天下,有杀主名。”王尚未自知当废,谓左右:“我故群臣从官安得罪,而大将军尽系之乎?”顷之,有太后诏召王。王闻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兵,期门武士陛戟,陈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听诏。光与群臣连名奏王,……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当废。……皇太后诏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诏,王曰:“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诏废,安得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送。王西面拜,曰:“愚戆不任汉事。”起就乘舆副车。大将军光送至昌邑邸,光谢曰:“王行自绝于天,臣等驽怯,不能杀身报德。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爱,臣长不复见左右。”光涕泣而去。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太后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出死,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光坐庭中,会丞相以下议定所立。广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诛,其子不在议中。近亲唯有卫太子孙号皇曾孙在民间,咸称述焉。光遂与丞相敞等上奏曰:“《礼》曰:‘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武帝时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躬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庙,子万姓。臣昧死以闻。”皇太后诏曰:“可。”光遣宗正刘德至曾孙家尚冠里,洗沐赐御衣,太仆以軨车迎曾孙就斋宗正府,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而光奉上皇帝玺绶,谒于高庙,是为孝宣皇帝。
明年,下诏曰:“夫褒有德,赏元功,古今通谊也。大司马大将军光宿卫忠正,宣德明恩,守节秉谊,以安宗庙。其以河北、东武阳益封光万七千户。”与故所食凡二万户。赏赐前后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杂缯三万匹,奴婢百七十人,马二千匹,甲第一区。
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光自后元秉持万机,及上即位,乃归政。上谦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
光秉政前后二十年。地节二年春病笃,车驾自临问光病,上为之涕泣。光上书谢恩曰:“愿分国邑三千户,以封兄孙奉车都尉山为列侯,奉兄骠骑将军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为右将军。
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太中大夫任宣与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赐金钱、缯絮、绣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玑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椁十五具。东园温明,皆如乘舆制度。载光尸柩以辒辌车,黄屋在纛,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陈至茂陵,以送其葬。谥曰宣成侯。发三河卒穿复士,起冢祠堂。置园邑三百家,长丞奉守如旧法。
初,霍氏指西汉权臣霍光子孙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爱厚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亡。”书三上,辄报闻。
其后,霍氏诛灭,而告霍氏者皆封。人为徐生上书曰:“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注:突,烟囱,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余各以功次座,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请之。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乡使福说得行,则国亡裂土出爵之费,臣亡逆乱诛灭之败。往事既已,而福独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贵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发灼烂之右。”上乃赐福帛十匹,后以为郎。
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霍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诛。故俗传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
赞曰:霍光以结发内侍,起于阶闼之间,确然秉志,谊形于主。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当庙堂,拥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权制敌,以成其忠。处废置之际,临大节而不可夺,遂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光为师保,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财三年,宗族诛夷,哀哉!昔霍叔封于晋,晋即河东,光岂其苗裔乎?金日磾夷狄亡国,羁虏汉庭,而以笃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将,传国后嗣,世名忠孝,七世内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为祭天主,故因赐姓金氏云。
老去情怀易醉。十二阑干慵遍倚。双凫人惯风流,功名万里。梦想浓妆碧云边,目断孤帆夕阳里。何时送客,更临春水。
男儿何用伤离别。况古来、几番际会,风从云合。千里情亲长晤对,妙体本心次骨。卧百尺、高楼斗绝。天下适安耕且老,看买犁卖剑平家铁。壮士泪,肺肝裂。
 蒋捷
蒋捷 李白
李白 班固
班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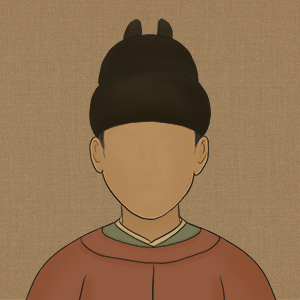 王衍
王衍 张元干
张元干 刘克庄
刘克庄 陈亮
陈亮 刘著
刘著 乔吉
乔吉 纳兰性德
纳兰性德 温庭筠
温庭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