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走出西直门,经过高梁桥,约十余里地,便到了元君祠。继而向北行进,可见一条长达十里的平堤,堤上夹道种着的都是年代久远的柳树,树木高低错落,相互交织掩映。那上百顷的澄湖,一眼望去,烟波浩渺。西山层峦重叠,与湖面波光相映成趣。远远望见功德古刹和玉泉山脚下的亭榭。那红色的大门和绿色的瓦片,青青的树林和苍翠的山峦,互相映发。湖中的菰蒲杂乱生长,水鸥和鹭鸶翩翩飞翔,让人仿佛身临江南水乡的画境之中。
我在金山寺和碧云寺、香山寺住了两夜,这天,骑着一匹驽马回来。我从青龙桥走上平堤,让马随心所欲地走着。这时,晚风正清,湖上的烟雾刚刚升起,那烟岚使人感到其中充满了水气,柳树正在枝繁叶茂之时,我在观赏的同时感到很快乐,几乎不愿离去。
在此之前,我曾约孟旋、子将同游西山,两人都不到,于是我便慨然独往。子将把西湖视为己有,眼界是真够高的,但他稳居七香城中,傲慢地对待我这次旅行,这是为何呢?我把这些写下来寄给在西湖的孟阳等诸位兄长,想博得他们一笑。
注释
西山:今北京西郊群山的总称,是游览胜地,包括玉泉山、灵山、香山、翠微山、卢师山等。
西直门:北京城的西门,城楼于1969年拆除。
高梁桥:在西直门外,因跨高梁河,故名。《长安客话》谓高梁河“水急而清,鱼之沉水底者鳞鬣皆见。春时堤岸垂青,西山朝夕设色以娱游人。都城士女藉草班荆,曾无余隙,殆一佳胜地也。”
可十余里:大约十里。可,大约。
元君祠:在西山妙峰顶,俗称“娘娘庙”。元君,道教对女性成仙者的尊称。
北:向北。
参差(cēn cī):高低不齐的样子。
掩映:或遮或露,时隐时现。一作“晻(yǎn)映”,有明有暗,相互交错。晻,昏暗。
渺然:渺茫不清的样子。
匌匒(gé dá):重叠的样子。此指西山连绵重叠的山峰。
功德古刹(chà):即功德寺,旧名护圣寺。刹,寺庙。
玉泉:即玉泉山,在北京市西北。以山下有玉泉而得名。山麓有静明园。
嶂(zhàng):直立像屏障的山峰。
缀发:相互映衬,相互引发。缀,联结。
菰蒲(ɡū pú):水生植物。菰,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在浅水里,开淡紫红色小花,夏生新芽,名茭白,秋结实,名菰米,可食用。蒲,水草,可制席。
信宿:连宿两夜。《诗经·豳风·九罭》:“公归不复,於女信宿。”
金山:指万寿山。
碧云:碧云寺,在香山上。其寺金碧辉煌,下有台阶数百级,气势恢宏,明代为京师诸寺之冠。
香山:香山寺,也在香山上。
蹇(jiǎn):跛,行动迟缓。借喻劣马或跛驴。
青龙桥:位于北京颐和园北宫门外,建于元代。
纵辔(pèi):放松缰绳由马随意行走。辔,驾驭牲口的嚼子和缰绳。
岚润如滴:山林中的雾气湿润得像要滴水似的。
顾:回首,回顾。
殆(dài):几乎。
去:离开。
孟旋:方应祥,字孟旋,作者友人。
子将:闻启祥,字子将,也是作者友人。
挟:怀在心里。
西湖:指杭州西湖。
顾:反而,却。
七香:本指多种香料的混合,这里喻指都市繁华。
孟阳:邹之峄,字孟阳,明万历间钱塘(今杭州)人。▲
赏析
这是一篇游记小品,如题所言“小记者,所以篇幅简在。丰富意味全赖精美语言体现,作者深谙此道,所以在遣画用语时将多重意义凝聚于一画一句之中。写游西山途经之地,作者颇吝惜笔墨,只用“出者“过者“至者三个动画,一笔带过,不肯多置一画。写到“折而北,有平堤十里者时,则又详尽铺写。近处的古柳、澄湖、菰蒲、鸥鹭,远处的西山、古刹、亭榭、青林,尽至笔端。作者用“掩映者“渺然者“缀发者“零乱者“翩翻者等一系列富有美感的画语,勾画出一幅充满野趣的江南图画。
作者在描述自己夜宿“金山及碧云、香山者时,使用了“看宿者这个画。虽然“看宿者看起来平淡无奇,但内涵却十分丰富富。东晋文学家袁崧在《宜都记》一文中,说他游宜都时“流连看宿,不觉忘返,目所履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者。可见“看宿者是因为流连不舍,如作者所言“顾而乐之,殆不能去者。“看宿者一画,既述宿两夜之事,又表达出对山水的留恋、崇尚之情。再看作者写昆明湖晚景。“晚风正清,湖烟乍起,岚润如滴,柳娇欲狂者,只四句便绘出一幅清新而又充满生机的图画。“柳娇欲狂者句是这一图画中的主体形象,昆明湖晚景的美色、灵性都蕴含在“娇者与“狂者两个画中。“娇者柔嫩可爱之状,有少女之情韵;“狂者自由随意,无所顾忌之态,有高士之风度。“娇者“狂者二字,既是昆明湖柳色,又是作者内心。作者用拟人笔法写柳态,使物性人化,人性物化,人与柳合二为一,景与情同至相生,令人佩服作者遣画用语之精妙。
但是有美景胜境,而无良朋相伴,实属遗憾,所以作者“慨然者而叹。“慨然者二字为全篇的文眼,丰富意蕴都从“慨然者二字道出。其一,明末清初钱谦益《列朝诗集》载:“长蘅居南翔里,其读书处曰活园,水木清华,市嚣不至。一树一石,皆长蘅父子手自位置。琴书萧闲,香茗郁烈。者又说他“性好佳山水者。可知作者对自然山水一往情深,且视自然山水为人生象征。在作者心中,山水已不纯粹是自然景观,而是有灵性有品格的活泼的生命,与尘俗秽杂正相对立。从“澄湖百顷,一望渺然。西山匌匒,与波光上下。……湖中菰蒲零乱,鸥鹭翩翻,如在江南画图中者等句,便可深知作者“慨然者之意。其二,与良朋佳侣同赏美景,乃人生一大乐事。西山美景,昆明湖胜境,固可赏心悦目,陶冶情性,然而没有良朋佳侣相伴,如作者所言“先是约孟旋、子将同游,皆不至者,难免生出遗憾。但作者的遗憾还不止于此。“子将挟西湖为己有,眼界则高矣,顾稳居七香城中,傲予此行,何也?者“何也者一问,使遗憾之义陡然升华。人处于山水之间,方能领悟纯静、高洁的境界,不亲历山水,何以能超脱尘俗。是朋友眼界高于自己,还是自己尚未达到真正的超脱境界?所以作者在结尾说:“书寄孟阳诸兄之在西湖者,一笑。者“一笑者虽为谐戏语,却意味深长。▲
创作背景
这篇文章应当是作者第三次赴京会试期间所作。作者原本邀请友人方应祥、闻启祥同游西山,但未能如愿,只好一人独往。面对西山美景,作者怡然陶醉,乐而忘返,即兴写下这篇游记,并作为书信寄给杭州的友人。
李流芳(1575~1629)明代诗人、书画家。字长蘅,一字茂宰,号檀园、香海、古怀堂、沧庵,晚号慎娱居士、六浮道人。歙县(今属安徽)人,侨居嘉定(今属上海市)。三十二岁中举人,后绝意仕途。诗文多写景酬赠之作,风格清新自然。与唐时升、娄坚、程嘉燧合称“嘉定四先生”。擅画山水,学吴镇、黄公望,峻爽流畅,为“画中九友”之一。亦工书法。
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或曰:冉氏尝居也,故姓是溪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谓之染溪。予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士之居者,犹龂龂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为愚溪。
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愚辱焉。
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
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如愚”,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今予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予得专而名焉。
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予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于是作《八愚诗》,纪于溪石上。
胖妓
夜深交颈效鸳鸯、锦被翻红浪。雨歇云收那情况,难当:一翻翻在人身上,偌长偌大,偌粗偌胖,压扁沈东阳。
春寒
春风料峭透香闺,柳眼开还闭。南陌蓑针不全翠,恨芳菲,上林花瘦莺声未。云兜香冷,乌衣何处?寒勒海棠迟。
上花台,落红沾满绿罗鞋。谁家庭院秋千外,兰麝裙钗。我闲将笑口开,也待了芳春债,何处把新诗卖。无情蝶怨,不饮莺猜。
湖上
夜游湖,翠屏飞上玉蟾蜍。粉墙犹记题诗处,树影扶疏。写新诗作画图,雪老西泠渡,花谢孤山路。林逋领鹤,潘苑骑驴。
梦中昨来逢君笑。把千年、蓬莱清浅,旧游相告。更问后来谁似我,我道:才如君少。有亦是,寒郊瘦岛。语罢看君长揖去,顿身轻、一叶如飞鸟。残梦醒,鸡鸣了。
 李流芳
李流芳 柳宗元
柳宗元 王寂
王寂 王和卿
王和卿 张可久
张可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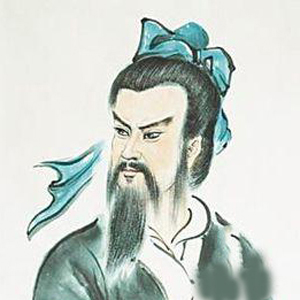 马致远
马致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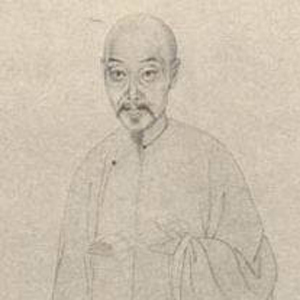 黄景仁
黄景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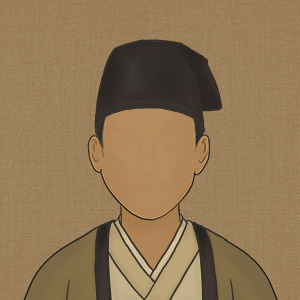 马咸
马咸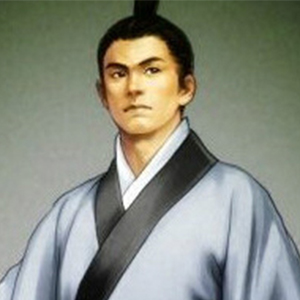 毛滂
毛滂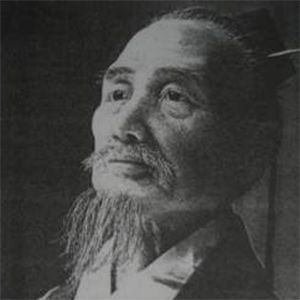 张元干
张元干 程垓
程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