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人们都认为孔子是大圣人,我也认为他是大圣人;人们都认为道教、佛教是异端,我也认为它们是异端。人们并非真的懂得什么大圣人与异端,因为他们是从父亲和师长的教导里听熟了的;父亲和师长并非真的懂得什么大圣人与异端,因为他们是从儒家先辈的教导里听熟了的;儒家先辈也并非真的懂得什么大圣人与异端,他们是因为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孔子说“圣人那是我不能够达到的”,这是他的谦虚。孔子说“讨伐儒家以外的其它思想”,这一定指的是道教与佛教。
儒家先辈根据主观猜测而作出上面这些结论,父亲和师长承袭和述说这些话,后生晚辈盲目地听从这些话。众人之口说着一样的话,是不可能被揭穿的;千年以来都是一样,人们自己都不知道。不说是“徒然无用地记诵孔子的话”,而说是“已经懂得了孔子这个人”;不说是“勉强把不懂当作懂”,而说是“懂了就是懂了”。到今天,即使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已没有什么用处了。
我是什么人呢?敢说自己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也只有跟随大家罢了。已经跟从众人而把孔子当作圣人,也就跟从众人而供奉孔子像,所以我跟随众人供奉孔子像于芝佛院。
注释
芝佛院:湖北省麻城市东十五公里的一座佛院,李贽在此著书讲学十余年。
老、佛:指道家与佛教。异端:不符合正统思想的观念和主张。这里指儒家以外的其他思想学说。
以:因为。
儒先:儒家先辈。
居谦:表示谦虚。
攻:攻击,批判。《论语·为政》:“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孔子时还未有道教和佛教,将此处的“异端”解为老、佛,说明这些“儒先”的无知。
亿度(duó):猜测。亿,通“臆”,料想。
小子:后生晚辈。矇聋:同“朦胧”。此句指盲目听从。
知之为知之:《论语·为政》:“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里指出道学家们只取孔子原话的上半句,装得一切都“知”,实则是“强不知以为知”。
目:这里指眼力,即明辨是非的能力。
圣之:意为把孔子当作圣人
事之:此处指供奉孔子的佛像。▲
创作背景
万历十三年(1585)春,李贽由黄安移居麻城,弃家只身住在环境幽静的龙潭芝佛院,从事著述、讲学,凡十馀年。这篇文章就是在芝佛院写的。
自汉代以来,孔子被神化。宋明道学家,把孔子当偶像来崇拜。明代科举,把儒家经书法定为考试内容。作者反对盲目尊孔,特写这篇杂文。
赏析
这是一篇带驳论性质的杂文,要批驳的中心论题是“人皆以孔子为大圣”“皆以老、佛为异端”。从而揭示出历代儒家之徒盲目尊孔的荒谬无知。——这本是个绝大的论题,千百年来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著书立说,是是非非,壁垒分明。但要把这个论题驳倒,却不是那么容易。李贽的这篇文章运用其特出的驳论方法和惊人的进步思想,十分出色地交出了一份答卷。
文章一开头,开门见山,以两个对出的分句揭示驳论的论题:“人”与“吾”皆以孔子为大圣,以老、佛为异端。“人”“吾”云云,意在指出人云亦云,世代相沿,成无异词,可见这种观点的普遍性与顽固性。然后作者予以驳斥。他不是采取正面立论驳斥的办法,而是追根寻源,层层推勘,找出“大圣”“异端”说的来历。原来持“大圣”“异端”说的“人人”,并不真的了解“大圣与异端”,而是从他们的父辈、师辈那里听来的,而他们的父、师们也不了解“大圣与异端”,而是从“儒先”们那里学来的,而“儒先”们也同样的不了解“大圣与异端”,而是从孔子那里传来的。再追查一下,原来孔子说过两句话:“圣则吾不能”和“攻乎异端”。其实,由“圣则吾不能”可见孔子并不承认自己是“圣”,更无“大圣”之说,而“儒先”们却一口咬定说那是孔子的谦虚,把“大圣”的桂冠硬是扣到孔子的头上;而孔子说的“攻乎异端”中的“异端”,由于在孔子的时候还没有出现奉老子为教主的道教和由印度传来的佛教,所以这个“异端”只能是指不同的见解、议论,而“儒先”们却一口咬定是指道教与佛教。经过这样的追根寻源,层层拨开迷雾,原来代代相传的“大圣”“异端”之说,竟是“儒先”们“亿度之言”,是无稽之谈,是他们捕风捉影造出的谣言。这就从根本上拆穿了所谓“大圣”“异端”说的谎言。这是一段绝妙的驳论。最有力的驳论,莫过于证明被驳一方所持的赖以形成其观点理论的材料证据是虚伪和错误的。
在拆穿了“儒先”们的谎言之后,作者正面发了一段评论。古人写这类文章,往往是有驳有论,既驳且论。本文第一自然段侧重于驳,第二自然段则主要是论。作者用“亿度而言”“沿袭而诵”“矇聋而听”,尖锐地指出了儒家之徒将一些“亿度之言”奉为金科玉律,代代“诵之”“听之”“万口一词”“千年一律”,愚昧懵懂而却自以为“知”的荒谬鄙陋。作者在《圣教小引》中有一段话可与这里的评论相阐发:“余自幼读《圣教》不知《圣教》,尊孔子不知孔夫子何自可尊,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研,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自笑也已。”这里,作者对封建社会传统的偶像和教条给予了大胆抨击,千年腐儒道统之弊,被一言道破。
李贽生活的时代,正是道学猖獗的时代。他的思想与言论在当时确有惊天动地、振聋发聩的作用。但世俗昏昏,如同无目。故作者认为,生于无目之世,“虽有目,无所用矣”!——既愤世嫉俗,痛心疾首,又痛感曲高和寡、世无知音。有目而不能用,应是世上最痛苦的了。所以,作者于文章结尾点题,再申此意。“敢谓有目?”有目而不敢承认,这是当时作者处于封建卫道者们的围剿之中,有目而不能用,一切只有“从众”而已:“既从众而圣之,亦从众而事之”,“事孔子于芝佛之院”亦是“从众”而已。短短几句话中,连用四个“从众”,意在反复申明:事孔子并非出于作者自己的意愿,仅仅是一种“从众”的行为。这样,就把“孔子像”置于非常尴尬的地位。而把这些话“题”在“孔子像”上,则与其说是“事之”,不如说是“批之”。李贽后期文章,笔削挞伐,或正面抨击,或侧面揶揄,皆独具剜心刺骨之力,“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袁中道《李温陵传》)。
李贽的驳论、辩难之类的文章,有其独特的写法。他自己曾说:“凡人作文皆从外边攻进里去,我为文章只就里面攻打出来,就他城池,食他粮草,统率他兵马,直冲横撞,搅得他粉碎,故不费一毫气力而自然有馀也。”(《续焚书·与友人论文》)这篇文章即“就里面攻打出来”,所用材料都是腐儒们的口头禅,连“从众”一词也是从孔子言论中拈来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而事半功倍,具有无可辩驳的批判力。▲
李贽(1527~1602),汉族,福建泉州人。明代官员、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李贽初姓林,名载贽,后改姓李,名贽,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等。历共城教谕、国子监博士,万历中为姚安知府。旋弃官,寄寓黄安(今湖北省红安县)、湖北麻城芝佛院。在麻城讲学时,从者数千人,中间还有不少妇女。晚年往来南北两京等地,最后被诬下狱,自刎死于狱中。其重要著作有《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史纲评委》。他曾评点过的《水浒传》、《西厢记》、《浣纱记》、《拜月亭》等等,仍是至今流行的版本。
秋风飒飒撼苍梧,秋雨潇潇响翠竹,秋云黯黯迷烟树。三般儿一样苦,苦的
人魂魄全无。云结就心间愁闷。雨少似眼中泪珠,风做了口内长吁。
虾须帘控紫铜钩,凤髓茶闲碧玉瓯,龙涎香冷泥金兽。绕雕栏倚画楼,怕春
归绿惨红愁。雾丁香枝上,云淡淡桃花洞口,雨丝丝梅子墙头。
恨重叠,重叠恨,恨绵绵,恨满晚妆楼;愁积聚,积聚愁,愁切切,愁斟碧
玉瓯;懒梳妆,梳妆懒,懒设设,懒黄金兽。泪珠弹,弹珠泪,泪汪汪,汪汪
不住流;病身躯,身躯病,病恹恹,病在我心头。花见我,我见花,花应憔瘦;
月对咱,咱对月,月更害羞;与天说,说与天,天也还愁。
乐府合欢曲
读《开元遗事》去取唐人诗而为之。一名《百衲锦》,因观任南麓所画《华清宫图》而作。驿尘红,荔枝风,吹断繁华一梦空。玉辇不来宫殿闭,青山依旧御墙中。
乱横戈,奈君何,扈从人稀北去多。尘土已消红粉艳,荔枝犹到马嵬坡。
岁东巡,洛阳城,天乐宫中夜彻明。不忆李暮偷曲去,酒楼吹笛有新声。
雨霖铃,却归秦,犹是张徽一曲新。长记上皇和泪听,月明南内更无人。
忆开元,掌中仙,入侍深宫二十年。长记承天门上宴,百官楼下拾金钱。
锦城头,锦江流,回望长安帝尽愁。那更血魂来梦里,杜鹃声在散花楼。
驿坡前,掩婵娟,惨乱旌旗指望贤。无复一生私语事,柘黄袍袖泪潜然。
九龙池,百花时,乐按《梁州》爱急吹。揭手便拈金碗舞,上皇惊笑勃妳儿。信音沉,泪沾襟,秋雨铃声阁道深。人到愁来无会处,不关情处也伤心!
 李贽
李贽 白居易
白居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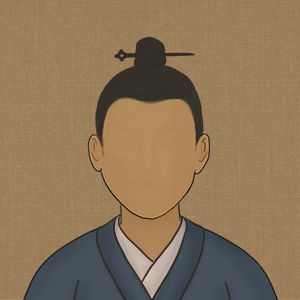 刘庭信
刘庭信 姚燧
姚燧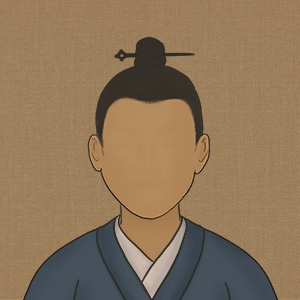 周文质
周文质 王恽
王恽 叶梦得
叶梦得 白朴
白朴 郑文焯
郑文焯 辛弃疾
辛弃疾 王炎
王炎